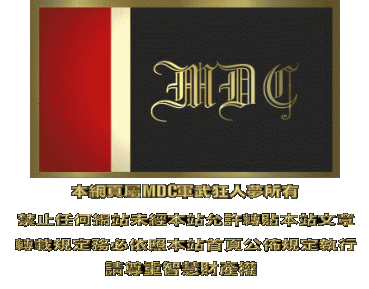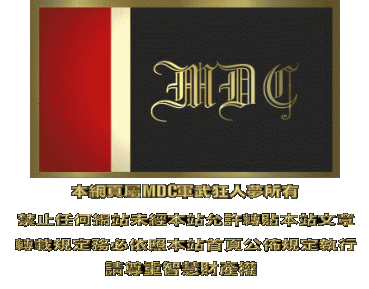
第四十轟炸機大隊轟炸南京任務
BySam
|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察費克德瑞的B-29超級空中堡壘機組人員在轟炸南京任務時遇難,轟炸機遭到了擊落,四人死亡,三人被俘虜,五名由中共新四軍救起。由於此資料對了解B-29執行對日本佔領區尤其是中國淪陷區轟炸任務的歷史相當珍貴,而且還涉及到了日本佔領下的南京與中共新四軍與美國飛行員的活動,因而本人將這篇口述歷史翻譯後,加上其他資料,以紀錄的方式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
B-29編號# 42-6237“Sir Trofrepus(德福瑞普斯長官號)”機組人員 官階 姓名 職位 下落 一等少尉 李察費克瑞德(Richard Vickery) 正駕駛 陣亡 二等少尉 伯那佩奇(Bernard Page) 副駕駛 陣亡 二等少尉 艾德華凱西迪(Edward Cassidy) 投彈手 陣亡 一等少尉 福雷克斯史耐可皮(Fleix Sinicrope) 領航員 去世 二等少尉 威廉華普頓(William G. Warburton) 飛行策劃官 二等中士 迪瓦克林斯(Dwight Collins) 雷達通訊官 中士 佛德瑞克克爾頓(Frederick Carlton) 中央火力指揮 中士 卡羅瑞吉(Carl Rieger) 右機槍手 中士 華特生蘭克福特(Watson Lankford) 左機槍手 中士 約翰邁爾(John Myers) 攝影官 陣亡 中士 喬治蘇奇爾迪(George Schuchardt) 尾機槍手 少校 法瑞斯摩根(Francis Morgan) 觀察員 去世 史耐可皮, 華普頓, 摩根, 克林斯與蘇奇爾迪在墬落後由中共新四軍救出,克爾頓,瑞吉與蘭克福特遭到日軍與南京政府的軍隊俘虜。史耐可皮與摩根已經去世,而 蘇奇爾迪與克爾頓還未被列入第四十轟炸機大隊協會的名單內,因為一直沒有尋找到他們的下落。
任務介紹: 與其他任務的執行計劃沒有差別,這是XX轟炸指揮部的第十五次任務, 主要目標是日本本土的九州大村,再來把目標轉向中國的上海,然後於南京結束任務。轟炸大村是在高空兩萬呎進行,任務執行大致與平常一樣,飛機於早上三點起飛。
湯姆卡羅爾(Tom Carroll) 是第四十轟炸機大隊的氣象官,他表示天氣會引響任務出發前後的執行情況!
湯姆卡羅爾的故事:在戰爭的條件下,我們的天氣分析圖是相當缺乏的,而且因為負擔過度的通訊技能,他們通常都較晚返回位於我們預先依照天氣預報在四川成都新津基地降落地點,事實上,我們預測的地點氣象都是十二到二十四小時以前的事情了。基於最新的氣象圖顯示,我們預計這次氣象很適合執行空襲九州的任務。 我當時剛結束對人員的轟炸簡報以後,我接到了一通來自氣象部門的的電話,他們告訴我福爾摩沙(台灣)東北部的氣象不安定,我問他們是否有告知氣象總部的人員此事,他回答說他也是從電話中才得知此事的,不過由於此天氣不引響我們的轟炸任務,所以我決定為我自己觀察一下天氣情況,所以我去了氣象部,那裡有現成的天氣分析圖。我發現台灣東北部的中度颱風正在朝東北方,也就是九州方向前進,並且會在投彈期間造成引響。到時候,九州上空會被層層的雲包圍住,視覺轟炸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於這份報告的來源不足,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那個颱風是否真的存在,更可以懷疑它的位置,強度,以及風向是否準確。看著我那一份不準確的前提報告,我認為九州不受颱風引響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應該九州的目標會非常清晰。不過糟糕的是,南京會被遮擋住。如果九州是晴朗的天氣,而南京卻是陰天,我告訴指揮官,我們從駝峰運來的燃料,炸彈以及其它物資盛至人員都有可能會被浪費掉,所以我強烈反對此項任務。我認為前提是寧願九州被遮擋住,南京則是晴朗的好天氣。我因次走向指揮塔通知布蘭奇(Blanchard)上校,當我趕到以後,最後一架飛機已經準備起飛,我立刻將氣象的問題告知上校,他要我將此事情重複給也在塔內的李梅將軍(General Curtis Lemay)。李梅被我關於天氣問題的打擾感到非常震怒,但是他並沒有立刻改變計劃,他開始計算他有多少時間可以要求機組人員改變計劃,並要求我持保留態度先,三到四個小時以後再來告訴他狀況是否改變了。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智慧的點子,我接著叫醒了轟指部的氣象員,讓他返回工作崗位。他顯得非常不高興,但是在我的證據之下,他也只有配合我的預料下回來工作了。
關於李察費克德瑞機組的敘述:機組人員在新墨西哥的克羅維斯展開集合與訓練,然後他們前往肯薩斯州海因頓(Herrington)接收一架B-29準備飛往印度。他們於六月底離開美國本土,由於氣象與其他方面的問題,他們直到八月初才到達了印度加爾格達。接著,組員們馬上被被分散。克林斯,蘭特福特,克爾頓,蘇奇爾迪與瑞吉被派去在印度克拉肯迪(Kalaikundi)飛C-109運輸機,其餘組員被安排為中國空運物資。十月底,組員終於被再度及合起來了,並且運送物資飛過駝峰航線一次,布蘭其應該是那次行動的飛行員,而費克德瑞是副駕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們被安排到了編號# 237的B-29執行此任務。機上共有八枚五百磅高空炸彈與四枚五百磅燃燒彈。然後他們將轉向南京。
福瑞斯摩根少校的故事:(摩根少校被派遣到XX轟炸指揮部,這次任務中擔任觀察員的角色,他再被救出戰俘營後把這個報告交了上來,福瑞斯摩根少校死於一九八四年)剛起飛不久,我們就發現油料由右翼的油箱流出,向機尾方向流去。我們將焦點放在機翼上面,認為可能是油箱的蓋子有破洞,所以我們朝A-1(註一)基地,但很快漏油情況就停止了,所以費克瑞德與策劃官華普頓決定繼續朝目標方向飛行。黎明時,我們抵達了集合地點,但是其他的機組已經集合完畢並且出發了。費克瑞德決定繼續單獨前進。當我們大體上航行到離中國黃海一百五十哩前,A-1通知我們大村的天氣非常混亂,因此所有機組轉回來去轟炸南京。我們轉向後,看到十四架飛機編隊飛行,但是我們沒有加入他們。費克瑞德決定由沿海經過上海一帶抵達南京,所以我們仍然在黃海上空。一個小時過後,我們仍然在海面上,華普頓告訴我們,就算我們沒有被日本人打下來,因為我們之前損失的那些燃料,我們也無法順利返回A-1。當南京出現在我們眼前時,我們順著風向飛行,大體上機體持一百七十度狀態飛行。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架戰鬥機,高射砲也還沒有反擊,但當炸彈開始投下時,我們聽到了防空砲彈擊中的巨響(機尾機槍手後來報告他在第四號引擎部位看到爆炸產生的火花)。克爾頓表示炸彈艙內的火太大了,因此他無法進入滅火。蘇奇爾迪也說道第四號引擎的火已經燃燒到了機尾。我們必須要待在飛機裡面直到我們遠離了日本佔領區。東京玫瑰(註二)警告了我們很多次,所有被俘虜的B-29飛行員都會被處死,而且我們有聽說過有人遭到日軍的折磨。華普頓緊接著告訴大家隨時準備跳傘,而大家都展開了回應。費克瑞德將飛機交由佩吉控制,華普頓遇到困難使鼻輪順利降下來迫降,直到幾分鐘以後才成功。我們接著失去高度,但還沒有失速,當飛機向右頃斗時,我們仍然再一萬九千呎高空,然後華普頓試著向後方人員們對話,但只有機尾機槍手蘇奇爾迪回應了。他告訴我們其他機槍手與雷達通訊官已經先跳傘了。當機身開始翻身時,領航員史耐可皮從起落架跳出飛機,接著是華普頓與投彈手凱西迪。費克瑞德與佩奇也開始試圖跳傘,但突然的一個大轉身將我們全部甩開,我與克林斯被甩入了策劃員的艙內,但是我馬上爬了起來抓住在我頭頂上方的鼻輪。蘇奇爾迪後來表示當他打開降落傘以後,他看到飛機經過他旁邊並慢慢地向右轉,連續轉了兩圈,接著四號引擎的火開始燃燒到整架飛機以及左翼,然後就在天空爆炸了。當我恢復意識以後,我發現我離地面兩千五百呎。當我試圖拉傘索時,我花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打開了降落傘。當我將眼睛旁邊的血擦乾淨以後,我發現兩個飛機的部位在我的左旁並且都在燃燒當中。碎片,鋁片與正朝我的方向從殘骸裡落下。然後我看到三面降落傘出現在我的面前,因此我向他們跑去。跑了三百碼後,我遇到了克林斯,蘇奇爾迪與華普頓。克林斯已經被飛機的旋轉給搞成休克,和我一樣奇蹟的逃生了,華普頓大概是唯一沒有受傷的人了。我受了臉部的傷害,包括被割傷且掉了牙齒,而且右臂有一個大切口。當我們有時間開始包紮前,一百碼外大約一百名武裝的中國人(註三)向我們這邊走來,並開始朝我們開火。我們立刻躲在稻田裡面尋找掩護,並且立刻發現我們被那群武裝的中國人包圍起來了,然後他們將我們的配槍沒收走了。他們表示我們必須要跟著他們走,所以我們就跟著走了幾哩,我們是早上十點被擊落的,直到我們走了十五哩都沒有停下來休息直到再走一哩後我才遇到了這支游擊隊的領導,並且得到了餵食。接著,我們遇到了史耐可皮,他是在津浦鐵路東方降落的,而我們則是在西方。
史料介紹:摩根少校表示飛機是被防空砲彈擊中的,但是其他人員認為是在投彈時與炸彈擦撞到,所以造成了爆炸以致飛機的損失。他們於二月十五日抵達了延安完成了撤退行動。到了隔年的三月三日,他們總算被送回了A-1然後轉到加爾格達,最後被送回了美國本土。
卡羅瑞吉的故事:當我們一起投下炸彈以後,炸彈在我們下方五十到七十五碼內爆炸,流彈打中了我們的右機翼並使我們的飛機起火燃燒。我是唯一能觀察損傷情況的人員,我發現炸彈艙內已經著火了。我回到我的位置(右機槍手),並用通訊器與其他組員聯絡,但沒有人回應,而情況則越來越混亂。六到八分鐘以後,我跳出了飛機,我是最後一個離開飛機後部的人員。我降落在稻田裡面,並扭傷了膝蓋與腳踝,然後降落傘再我跌倒以前把我拉到稻田的另外一處,也就是唯一有水的稻田地區。很快的,有十二個中國士兵(註四)向我跑來,我以為我得救了,但是他們搜尋我,並將我抓起來行軍走了兩哩到達了一個小房子。兩個小時以後,一組日本士兵趕到,把我帶起來行軍到了日軍的房子。他們第二天一大早就烤問我,但是我只給了他們我的名字,官階以及編號,即便他們拿著刺刀離我的眼睛僅有四英吋,並威脅要將刺刀刺入我的眼睛內讓我變成瞎子。我當時認為至少我們的部分機組人員避免了搜捕。然後接著一大早,日本人把我帶到外面去,我遇到了左機槍手華克生蘭特福特,然後我們被安排上了一輛火車,開了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抵達了南京,雙手被綑綁展開遊街。一開始我們走在最前面,但因為我扭傷腳的關係,他們讓我們搭黃包車(註五)。在黃包車內,一個中國小孩子走過來狠狠的打了我的頭一下(註六),接著管理的日本人馬上痛毆了那個小孩一頓。然後,我們被帶到了一個廢棄的大學校園內,入口處有一個警衛室以及兩個8x8的牢房。我們的手終於被鬆開了,然後我與蘭特福特被安排到這些牢房內。第二天,日本人再度審問我們,後來的兩個禮拜每天都是一樣的。我從來不跟他們說任何事情,因為事實上我知道的也不多,然後日本兵就會拿槍托打我的頭,膝蓋以及穹窿來找我麻煩。我的拇指被繩子纏在後方與樹枝綁在一起,然後被逼站在一個凳子上面,然後繩子綁得非常緊,凳子因為重量而往前移動。我的拇指痛了一個星期,但並沒有造成永久的傷害,接著我又被帶回去審問,由於我最後終於說服了他們我不知道任何東西,所以他們問了我一些他們自己的問題,包括我們的基地地點在哪裡。接著,他們總算是放過我了,我與華克生蘭特福特被關在一個相接的牢房內,但不允許我們對話。一但我們說話,警衛就會向我們潑冷水。我們冷斃了,因為沒有被子,沒有床也沒有軟暖流,只有我們的飛行服可以穿。十二月十日,我們兩人各得到了一片被子,我們的食物是一個杯子的白米每天三餐。有一天他們燒了米給日本人吃,並也分了一部份給我們,那已經是我們最棒的饗宴了。十二月三十日,我們又加入了福瑞德(福德瑞克)克爾頓被火車送到了上海附近的江灣戰俘營。這個戰俘營關了大約一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威克島戰役中被俘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與平民,也有美國北平大使館裡被俘虜的陸戰隊員。我們在這個監獄裡洗了自跳傘之後的第一次澡,並有美國醫生幫我們除虱並做健康檢查,我們接著被隔離並不許與其他俘虜對話。第二天(三十一日),六名新的俘虜被送了進來,其中一個是詹姆士馬漢(James Meehan),一個四四四中隊B-29轟炸機的機槍手。到了二月十八日,又有三名戰俘被衲入了戰俘營,其中一個是一等少尉佛那史佛(Vernon Shaefer),另外兩個到了四月十五日才被送了進來。他們大部分都是來自第十四航空隊不同戰鬥機單位的飛行員,階級最高的是第二十三大隊第七十五中隊(註七)的唐那卡利中士(Donald Quigely)。
歷史介紹:一九九一年美國國家檔案庫出版的“序言(Prologue)”雜誌中一篇關於威克島俘虜投降後的章節表示鄰近上海的江灣戰俘營擁有十分眾多的非戰鬥人員俘虜,由於日本人知道這些不同國家人民對日本的重要性,所以待遇比起其他戰俘營要好得多,尤其是比起緬甸的,日本本土的戰俘營則無法被觀察到情況。紅十字會被准許在戰俘營內活動,並可以送包裹給戰俘們。
卡羅瑞吉接下來的故事:與其他戰俘營相比,這個戰俘營的條件好多了,國際紅十字會的人員在此地活動,我們被安排住在一個類似營房的建築內,除了使用benjo(公共廁所)外,我們很少被准許外出。卡臨中士知道如何玩橋牌,並教我們如何玩,我們玩了好幾個小時,這是唯一能防止我們發瘋的方法了。 我的體重由十一月十一日的一百六十磅下降到一百三十磅,然後五月九日我們整個戰俘營被遷移到了北平郊外的豐台後又回升到了一百四十磅。我們由貨車運輸,車門由帶刺的柵欄連接了起來,日本警衛坐在中間,戰俘們都坐在後方。在這個戰俘營內,我們被安排住在倉庫內,到了六月二十八日,我們上了一艘船,大約有一千多人,整艘船沒有足夠的艙位容納每一個人。在十到十二個小時內,我們沒有領到任河水與食物,直到我們抵達了日本本州山口縣以後。到了山口以後,我們被安排坐火車北上九州之旅。在途中,我們看到了期待以久被B-29摧毀的廢墟與火光,但是我們不敢笑。在東京,日本警衛開始把我們分散開來,我與兩百人一組被分配到北本州,然後接著我們住進了一個又新又大的營房內。這是仙台第十一號戰俘營,離日本青森距離約十二哩。我們營內有一名威廉佛利(William Foley)少尉,他是駐北平武官中的美國海軍軍醫。另外有一百九十多名平民老百姓以及我們這組人馬。克爾頓,蘭克福特,馬漢,渥特(唐納渥特(Donald Watt)中士,一名C-47的勤務兵)與我,我們五個被佛利命令去看管平民百姓.,然後立刻被送區挖凹禿不平的礦山。這是一個很糟糕的營地,辛苦的工作,又野蠻,食物少,馬上體重又降到一百二十磅。八月二十日,日本人停止派我們去作工了,然後到了二十四日,日本人告訴我們終戰(投降)的事情。日本人與我們一樣開心(註八),然後由我們開始接管戰俘營了。接著幾天以後,B-29與美國海軍的低空轟炸機向我們空投了更多的食物,所有人都吃了他們所能容納下的食物,然後嘔吐,接著又再吃。我們於美軍取得了聯繫,並於九月十三日在仙台見到了他們,接著我們知道戰俘營管理官於八月十六日切腹自殺了(註九)。接著一艘英國驅逐艦把我帶到橫賓,然後我會搭上了一架C-54運輸機把我帶到了沖繩島,硫磺島,關島,瓜加林島,約翰遜島以及夏威夷。預計九月十九日到達了舊金山,不過我再關島的一家醫院被迫停留了十二天,實在是遭透了的經驗,但是我還是全身而退了,並且恢復了體力!直到今天我的身體然健康得很呢。
華特生蘭克福特的故事:我於一九四二十一月十一日(正好是南京任務的兩年前)由我那農村般的家鄉喬治亞州進入了部隊,我在邁阿密受了基本訓練,然後送到了密西西比州加爾夫波特,伊利諾州尚努諾,然後到了西雅圖的波音技術場,在我們離開尚努諾到西雅圖之前,我們被告知一但結業後,會以軍官階級服役,但這始終沒有發生。我們在西雅圖勞里基地受訓,然後轉移到了克勞維斯。我們在那裡集合並接受B-29的訓練。除了B-29之外,我們也在B-17內受訓,但每三到四天我們就會飛一次B-29。身為一名B-29的機組人員,我們被派到肯薩斯州的海因頓去接收一架B-29,飛行累積二十五小時經驗後,就準備飛向海外了。我們帶著一瓶燃料鈷(CO.2)一起飛行,卻毀壞了安定翼,因此技術人員要求我們換一個安定翼。由於我們已經離行程計劃遲到太多了,所以他們寧願幫我們換一架新的飛機而不願意讓我們在這裡等。而另一架飛機性能並不比舊的好,但是我們依然準時前往印度,經過西棕灘,巴西,非洲,我到了印度卡拉齊以後就因長途跋涉住院治療了。到了八月,我們終於抵達了加爾格達,並被分配去做不同的工作。有一些已經飛過不少任務的中士由於離開了任務,所以我們有機會 飛他們的飛機。我們組員抓住這次機會來讓我們加入戰鬥任務,並且進入戰爭狀況,當我們接受到轉航到最後一個目標南京執行任務時,我們正在前往大村的航程中,因為我們被警告那裡有很多防空砲與戰鬥機。(註十)費克瑞德在海岸上空往北飛行,企圖與機隊混合,最後,策劃官告訴他我們必須直接飛往目標,否則沒有足夠的燃料返回基地。費克瑞德因此要求領航員給他由南京返回A-1的方向。當我們抵達目標上空以後,整個區域被雲層包圍住,因此雷達通訊官被通知執行雷達轟炸,但兩分鐘以後,投彈手表示炸彈已經恢復清晰了,所以可由他來執行。我們機槍手被交代過要觀察炸彈擊中目標的情況,當投彈手大叫“投彈(Bombs Away)”後,我們立刻傳出“你們有沒有看到炸彈的下落”之類的話,接著炸彈從機體下方爆炸打斷了我們的情緒,右翼的油箱起火爆炸,整個機翼起火燃燒。我們接到了副駕駛用無線電的通知保持待命,然後我們的雷達官說他要離開這裡,他拿起斧頭把吊門砍壞跳出飛機,克爾頓,瑞吉與我排隊往後艙口跑去,我們的隊伍裡由克爾頓走最前面,因為他是中央火力指揮官,我在他後面直到我被推出去為止,然後瑞吉也跳了出來。四個引擎都還在運作當中,我們並沒有接到命令跳傘。當我抵達地面後,我開始企圖掩埋我的降落傘,直到一些中國人士兵走過來,我以為他們是我的友軍,因為他們是中國人,但是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把我們交給了日本人。我被帶到了南京的一個監獄,在那裡,我遇到了卡羅瑞吉。雖然我們在可以對話的距離,但我們看不到對方,警衛除了一位外,都不允許我們講話,而那一名警衛到了一定的時間會准許我們對話。我們被帶去審問,我被審的道不嚴重,但我們都被告知“如果你們說謊,你們必死無疑”。其中一個日本審問員是一個日裔美國人,他從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畢業,於一九四零年被日本邀請回國擔任日本翻譯與審問員。他問我如果我換成他的情況,我會怎麼做,我為了與他玩把戲,告訴他我會跟他做同樣的事情。他問我覺得誰會贏這一場戰爭,我告訴他他自己心理應該明白,但他卻說他還不在預知戰爭結果的立場當中。在南京待了五十一天沒水洗澡的日子以後,我們被送到了上海的戰俘營。我們的待遇好了一點,我們有了洗澡,刮鬍子與整理的機會,我得到了六個紅十字會的包裹,雖然他們沒有多大的能力,但是我們足夠從他們那裡得到物資上的補給了。那裡還有不同國家的居民,包括義大利人與羅馬利亞人,以及在威克島以及美國政府號招前往的其他屬地被俘虜的居民。B-25,B-29以及戰鬥機飛行員,海軍醫官都與我們關在一起。從上海,我們被轉移到北京,然後準備被船運到日本本州,然後我們經過東京抵達本州本部的戰俘營。我想我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時我人在東京,那裡已經被燒得一無所有了。除了鐵路與港口旁邊,幾乎沒有一棟站立的建築物,然後我們在本州的監獄經過了一段飢荒期。 突然,戰爭結束了,一名官階最大的海軍醫官少尉掌控了大局,並要求日本人提供我們肉類食品,所以日本人就帶進來了一隻活的小牛。當B-29轟炸機發現我們,並提供食物拯救我們以前,美國海軍航空母艦斑尼頓號的俯衝轟炸機已經開始空投食物給我們了。我們接著到達了佐士保,我們搭上了一艘醫護艦,然後又換了一艘到達馬尼拉。最後搭乘一架C-54直接飛往舊金山,住進了萊特門醫院,經過一段時間的醫療以後,我回到了我今天居住的喬治亞州。
迪瓦克林斯的故事:我們的飛機在目標南京進乾船塢正上空起火燃燒,那裡有一些分散的防空砲火,但是先跳傘離機的機組人員則認為是炸彈在機機下方爆炸引發大火,而非防空砲彈。我們這些在前艙的機組人員則盡量避免再敵人佔領區上空跳傘,而這是一個不幸的決定,因為費克瑞德隊長,佩奇少尉與凱西迪少尉沒有成功跳出飛機。史耐可皮是第一個從後艙逃脫的組員,我想摩根中士是第二人,再來是華普頓少尉從艙口逃出,接著右翼斷裂,飛機開始向下墬落,我最後記得逃生洞口在我的上方,因此我使出吃奶的力氣往那移動,但地心引力太強大了,我開始被拉往地上。接著我試著猛力一拉打開降落傘,我還記得我看到水流在我的腳底下,並認為自己會降落到水裡去,但後來我發現那只是在稻田裡面的水而已,因此我只落在岸邊。從史耐可皮的紀錄當中,當他打開降落傘以後,機翼開始斷裂,然後往下墬落轉了三圈以後爆炸變成一百多面碎片。我的頭髮與眉毛有被燒到,但是我的皮膚沒有被燒傷。不用多說,我呈現了休克狀態,華普頓少尉是第一個跑來與我接觸的組員,他幫助我止住左額頭上方的血跡。我們接著看到小山丘上有日軍巡邏隊向我們跑來並開火射擊,我們一起跳入水溝內,並且不知道夏一步該怎麼做。突然,有十到十二名中國游擊隊員出現在我們的水溝旁邊,並開始向日本人還擊。有三到四人跟我們表示跟著他們由水溝地道下離開此地。到了上午十一點,他們突然要我們快速撤退,留下一批隊員在我們降落的稻田地帶與日軍對抗直到我們遠離為止。到了晚上,我們經過叢林,到達了一個小泥屋,然後我們翻倒在地上。他們讓我們睡到午夜,然後叫起我們並餵給我們吃熱湯,並比畫告知我們該離開了。我們的“比畫書”(註十一)接著起了作用,我們指著一行字微笑的問他們是否能送我們返回美軍基地。他們點頭肯定的表示只要在翻過一個山丘就會抵達目的地。由於我的鎖骨脫臼又有血流出來,造成我無法順利呼吸來走這麼長一段的距離,所以他們讓我們騎上了驢子,然後兩名士兵在我的左右兩旁扶住我。我們在沒有月光的晚上繼續前進,接著我在驢子上的骸骨傳來了比我鎖骨與腔部還疼痛的劇痛。我想那是所有跳傘沒有被俘成員會合前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接著幾個月的旅程以後,我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我們往西走以後仍然在敵佔區四百哩內。我來提一提那群中國游擊隊士兵,因為這就是他們鬥爭的方法(註十二),事實上,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新四軍,當初有中共控制了兩支部隊,分別是八路軍與新四軍(註十三)。他們告訴我們,國民黨的部隊拒絕接受被中共軍隊拯救的美國飛行員,因為之前被中共拯救的美國飛行員交還給國民黨軍隊以後,美國飛行員都會向美國情報機構抱怨國民黨部隊的無能以及抵消極抗日政策(註十四)。不管這些是否屬於實話,但是我仍然發現,中共帶我們經過他們的管區往北前往延安,確實延長了我們的距離約兩百多哩。我知道再延安有一組美國代表團(註十五)處理索回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從來沒有與他們有過本身的接觸,但是救助我們的士兵有用通訊機報告我們的名字,階級以及編號給美方代表。掩護我們的中國士兵有時候只有十到十五人,因為我們在安全的淪陷區地帶。有時候,我們要在一個地方待上兩到三天等待更多士兵來支援我們走較有威脅性的日本控制區。有一次,一組中國騎兵帶領我們快速在兩天內通過那個區域,因為那裡有不少日軍進駐。當我們要經過鐵路線時,我們就被掩護的更緊了。我們被給予了與中共部隊同樣的衣服與軍服(註十六),以免顯得明顯。當我們抵達了一些安全的村莊時,他們會帶我們引見一些地方官員,我相信他們是那些地區的共產黨主要政治人員。這些聚會都是以宴會的方式舉辦來表揚我們,他們主要是要表示我們可以引響美國未來對華實行武器與彈藥支援時的分配工作(註十七)。從南京走到這裡,我盛至懷疑那些參加的人每個都知道我們是美國飛行員。階級最高的摩根少校經常代表我們說話,他們每次都希望他能在聚會裡說話。少校的話語都打轉在讚美與宣揚他們對戰爭的引響,他們的地方小鄉鎮,以及我們看待日本即將敗亡的命運。換句話說,他的外交語調讓翻譯可以任意告訴中國代表們他想要說的話。很多場合中,翻譯說的話都遠比少校本人說的多。在一個場合裡,翻譯告訴少校在宴會裡發言,少校問他“你想要我說什麼?”,但翻譯回答“任何話都行,我已經把我的劇本寫好了”。這種中國人向我們敬酒的宴會久而久之對我們而言就成習慣性了,我們並沒有被優先敬酒,而是我們向他們先敬酒。有一次,翻譯還變“強硬”了,他開始在兩方都沒開口前就代表少校以及中國官方代表說話了。當我們經過平靜的小鄉村時,有一天,我們看到了一隻兔子。華普頓少尉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大叫發出聲音,兔子就會待在那裡不動。我不知道在他的家鄉芝加哥的兔子是哪一種,但是中國的兔子並沒有待在那裡不動,而是我們停在那裡大叫了一個多小時的追逐期間。 有一次,我們住在一個村外的小泥屋,翻譯告訴我那這個地區有很多日本兵,所以要我們最好不要外出。我們晚上經常被窗戶旁邊的老鼠吵醒,我們一直以為是有人要闖進來,所以配槍都不離手。所以每個人都拿起配槍往窗戶安靜地走去,然後就看到一隻老鼠在月光照耀的窗戶下,然後大家因而放心的又回去睡覺了。有趣的事情不斷的發生,有一晚在另外一個村子裡面,中國的和尚打著大鼓讓我們睡不了覺。第二天我們問翻譯發生了什麼事,他告訴我們和尚打著大鼓去安慰一隻受傷等待治療的水牛,因此我們要求翻譯帶我們到那裡去看一下。很快的,再另一個泥屋們裡面躺著一隻水牛,和尚與水牛的主人在。他們要我們為受傷的水牛說一點話,我要為隨時能夠增加場面氣憤的華普頓少尉加分,他要我們手牽著手圍著水牛唱“嗎啡鍾(Morphine Bill)”與“古柯鹼蘇(Cocaine Sue)”(註十八),結果第二天水牛起來並開始吃草了,所有的中國人都來到我們的泥屋向我們道賀並感謝我們拯救了他們的水牛。最後,我們終於抵達了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大本營延安。我們被告知會有一架飛機在一個計劃好的日子上午十一點戴我們離開這裡。在我們準備被接走的前一晚,延安下雪下的大約六到八英吋。我們被告知除非我們要飛機取消航程,否則我們必須清除跑道上的雪,在吸引日本戰鬥機威脅下起飛(註十九)。我認為我們已經見識並經歷了太多冒險,因此要求整理跑道。馬上,整個跑道上堆滿了幾百名中國人。他們企圖將雪從跑道上清乾淨,好讓我們的飛機可以降落。並不是每一個都有鏟子可以工作的,他們有些使用的是木板,水桶以及煮飯的用具,但成效不大。大約兩到三個小時以後,跑道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將雪放在稻草上,然後燃燒出大煙吸引飛機的注意。當預定時間一到,一架解除武裝的B-25轟炸機降落到了跑道上,然後四架P-51在上空提供掩護,然後B-25就像降落在芝加哥的奧克爾機場(註二十)一樣容易的落在延安的跑道上。當我們準備登機時,P-51仍然在高空提供掩護,這給了我們極高的愛國心,並且知道一個人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來引響並奉獻戰爭中的國家,而他的國家也會做很多事情來引響並拯救他。我們一共有九個人搭上B-25,三個是飛美國運輸機墬落的,一名是戰鬥機飛行員在掃射鐵路時被日本人打了下來,所以他們是來與我們會合的。我們飛回了昆明,接著被美國情報機構訊問,中國人給了我們一張日本兵力配置圖,而海岸線則是有日本重兵埋伏的地方,這些情報似乎相當有用。接著我們接到了被送回美國的命令,然後在華盛頓特區與維吉尼亞州的情報基地對已經輕鬆並可以說話的我們進行了審問,因為我們的胃部在過完吃米酒的日子後終於有了無限的資源。我告訴威爾羅吉斯(Will Roges)“我還沒有見到過一個討厭的中國人。”
後紀 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文章,裡面描述了江灣戰俘營的生活,以及南京政府軍的如何參與日軍圍捕美國飛行員的行動,算是相當不錯的了。裡面也描述了美國人對新四軍的看法,也讓身在台灣的我們能夠了解中共抗日中的戰術,算是值得一讀的,而且我們也發現,台灣地區的颱風真的是很可怕!
註一:當時美軍部隊給成都四個B-29基地取了不同的代號,A-1(新津),A-3(廣漢),A-5(雙流)與A-7(彭山)。
註二:東京玫瑰本名愛娃戶栗,日裔美國人,二戰時期為日本宣傳對工作,以性感優雅的英文在美軍中打響了知名度。日本投降以後,被以叛國罪褫奪公權,到了一九七七年由福特總統赦免。
註三:應該指武裝的中國農民,一般而言這是游擊隊基本的服裝。武器應該是從日軍與南京政府軍手中繳獲而來的。
註四:這些是南京政權的和平軍,也就是熟稱的“偽軍”。他們的制服是日本式的,但帽徽上也是青天白日徽,所以讓不知情的美國人很容易上當而遭到逮捕。和平軍大多是投降日軍的國軍雜排軍與華北維新軍組成,大部分戰鬥力很弱,但南京周圍的較強,而且比較忠於“日中親善”的原則。不過與日軍的衝突經常發生,他們某一方面確實也做到了保護中國居民的工作,主要掃蕩敵人是新四軍與轟炸淪陷區的美國飛行員,而非直接用於作戰。抗戰勝利以後,有一部分被國軍收編(但很多之後又投共),其餘大多被國軍排擠,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成部分之一。
註五:黃包車就是人力車,在中國很有名的交通工具。
註六:南京政權的教育下,美國人是與新四軍才是侵略者,所以小孩子打美國飛行員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以後的七年以後是有可能,要不就是小孩子以為坐在人力車上的是日本人,因為民風未開嗎。
註七:第二十三大隊七十五中隊是駐華空軍特遣隊早期三個中隊的其中之一,也是最早到中國作戰的美軍單位之一,請參考我的雲南驛與豫湘桂空戰作品來了解這第二十三大隊以下的幾個單位。
註八:飽受戰爭之苦的日本人對於戰敗雖然不甘心,但是能結束戰爭還是最好的。
註九:長官對於戰敗還是必須以切腹一刀了斷,比起海外的日本士兵,本土的日本兵不用一起“玉碎”,算是相當幸運的了。
註十:美國B-29轟炸機大多會先空襲一個地方如大村來吸引其他地方的日軍注意,再返航時可能會順便轟炸另一個擁有高防禦能力城市,因為已經被之前的空襲吸引住了,所以即便擁有戰鬥機與高射砲,日軍與南京政府軍也無法即時反應過來。
註十一:“比畫書”是類似“來華助戰洋人 軍民一體救護”的血書的一張說明書,上面有中文與英文,美國人只要指著那一行字就可以與中國人作簡單的溝通。這是美國對淪陷區展開攻勢以後而大量採用的。
註十二:游擊隊鬥爭的方式就是在淪陷區培植大量的根據地,然後經過這些根據地繞遠路與總部通訊,而非走大路,否則就是與日軍正面衝突。
註十三: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以後培植的兩支軍隊,大部分時間在淪陷區活動,一九四零年以後與國府軍決裂,不過與美國人的友誼並沒有因此斷裂。抗戰八年中,以八路軍的活動較為活躍,支援過平行關戰役並發動過百團大戰,而新四軍主要是在華南培植勢力對抗日軍,南京政府軍與重慶國民政府第三戰區的掃蕩,兩軍都在三方壓力下拯救過不少美國飛行員。不過,他們真正的目的仍然是在抗戰勝利後與國府軍一決雌雄,而非單純的抗日救國。
註十四:確實有不少美國飛行員上了中共統戰的當而誤認中共才是抗日的主力要求美軍以中共為主支援中國抗日,但個人認為他們把偽軍與國軍混唯一談了,不過當初國軍確實也有把美援武器留下來打共產黨,而不給前線雜排武裝武器的事件,造成史迪威與中共可以宣揚“中國不戰論”。
註十五:應該是包瑞德將軍率領的“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也就是美軍駐延安觀察組。
註十六:一般是農民的衣服,新四軍的制服是灰藍色與國軍一樣,左臂佩帶“新四軍”以作區別。宛南事變(新四軍事件)以後,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被取消掉了。
註十七: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他們是在幫延安爭取美國人支援武器,並希望美軍以延安為在華的主要合作對象。
註十八:那些是美國名搖,安慰即將死去的人而作的歌曲。
註十九:日本陸軍航空隊自從一九三九年以後就再也沒有對延安實施空襲了,海軍航空隊就更別說了。
註二十:奧克爾機場與中途島機場是今天芝加哥兩個主要的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