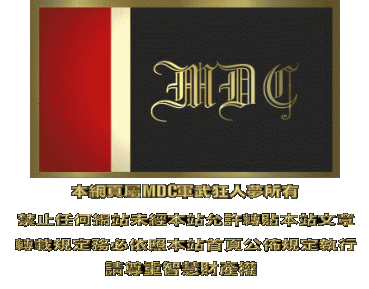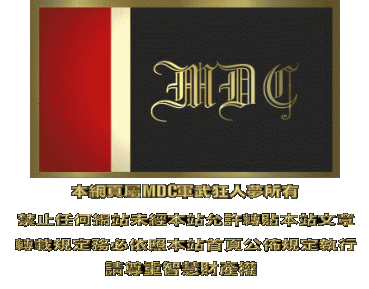
衝突、危機、失控、戰爭:「七月危機」的省思與啟示
作者:高慶先
一、
前言
1914年8月4日,德國陸軍「繆斯軍團」(Army
of the Meuse)的混成兵力對比利時的列日要塞展開攻擊(註1)。是此,「中歐同盟」與「協約國」雙方兵力正式交火,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此拉開序幕。
是何種力量牽引著擁有共同價值與信仰體系的歐洲國家從相互仇視到兵戎相見,以致最終走向自我毀滅之途?自1905年以來,歐洲國家曾因「摩洛哥危機」幾乎濱臨戰爭邊緣,而巴爾幹半島諸國的混戰更使國際局勢空前緊繃,在主要國家的克制之下,這些危機終究是安然地渡過。但「薩拉耶弗事件」不同,這不僅是因為奧匈帝國儲備領導人遇刺事件所突顯的:對維也納當局在波、赫兩省統治權正當性之直接挑戰;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它將俄、奧長久以來在巴爾幹半島的矛盾與衝突白熱化,甚至透過結盟外交體系的結構向外延伸,使歐洲主要國家均難以置身事外,而大幅提高了歐洲國家處理「七月危機」的困難度。
八十年後的今日,巴爾幹半島依舊因為民族問題而戰火不斷,戰爭似乎並未因兩極對抗的結束而減少,甚至消弭。相反地,過去因東西對抗而遭到壓抑的矛盾與衝突,反而因冷戰的結束而得以解除束縛(註2)。克勞塞維茨曾言:「欲求和平,必先了解戰爭。」因此,我們有必要將「七月危機」的始末作一次回顧與檢討,這不僅是為了省思過去的教訓,甚至對於今日我們身處環境所可能面臨的挑戰,亦是極具參考價值的經驗。
二、「俾斯麥體系」崩潰後,歐洲結盟外交的矛盾與衝突
曾經有一位英國史學家說過:「當德意志統一,歐洲各國都將驚駭不已。」「歷史上的德國,不是太弱,就是太強,對歐洲和平毫無助益。」
此評語傳神地描述了德意志統一之初,歐洲國家是如何疑慮與不安地觀察德國統一後的外交動向。基於七十年前的經驗,歐洲各國領導人普遍相信德國將會依循拿破崙的路線,開始無限制的權力擴張。而當權力過度膨脹,最終必然走向崩潰。俾斯麥深刻明白德意志的統一並不受到歡迎,法國雖於色當之役戰敗,然而卻隨時有復仇的可能。因此,德國的安全必需建立在一種與英、俄保持和睦,而同時又能夠 不讓法國有復仇機會的國際架構之下。換言之,就是一種「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註3)。「俾斯麥體系」的目的,是以柏林為戰略天平的中心,期望透過一種精心設計,以「德俄再保險條約」(The
Reinsurance Treaty)與「地中海三國同盟」(The Mediterranean
Agreement)為基礎的交叉式權力平衡運作來孤立法國,杜絕法俄結盟的可能,進而確保德國的安全。事後證明,這種安排相當地成功,「俾斯麥體系」在維護德國安全的基礎上,的確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然而隨著1890年俾斯麥的下野,在威廉二世尋求改變德國外交政策的強烈企圖下,維繫德國安全近二十年的「俾斯麥體系」終於土崩瓦解。原先以冷靜、謹慎、細緻的手段來緩和歐洲各國對德國的疑慮以保證柏林在國際政治的地位與安全的外交指導,被激情、粗略、擴張式的領導所取代。
制約俄、奧巴爾幹衝突的運作機制蕩然無存
「俾斯麥體系」崩潰的立即性結果,不僅僅是法國成功地突破了外交孤立,而促成1894年法俄同盟(The
France-Russian Alliance)的形成(註4)。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德俄再保險條約」的中止更意味德國從此將無法制約聖比德堡未來任何在鄂圖曼帝國與巴爾幹半島的權力擴張。特別是俄國對巴爾幹半島的權力追求將與奧匈帝國的安全與利益相互碰撞,在威廉二世從更親密且堅定的態度重申「德奧同盟」(The
Dual Alliance)的基礎上,這項保證鼓舞了維也納當局尋求更強硬的巴爾幹政策(註5),無形之中,亦將柏林與維也納的命運緊密的連繫在一起。一旦該區域因俄、奧的權力競逐而發生衝突時,德國將不僅缺乏外交調停之第三者所需具備之威望與立場中立,也將因與德奧關係過於緊密而捲入衝突。
英國放棄「光榮的孤立」:歐洲正式進入緊密的集團對抗
大幅擴張海外殖民地事業構成了威廉二世外交政策中相當重要的環節,這似乎是民族主義的激情,而非一種基於冷靜思考的結論。德國與英國在近東、非洲、遠東地區的殖民競賽勢必將導引英德關係從「合作伙伴」質變為「競爭對手」。
為了確保海外殖民政策的成功與安全,德國海軍艦隊的規模必須進一步地擴充,於是「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註6)產生了效應。基於維護帝國生命線的安全,英國海軍被迫針對德國海軍日益增強的威脅加速其造艦計劃。在英國「兩強標準」〈Two
Power Standard〉的軍備政策下,德國海軍的擴充陷入了既無法建立可與英國海軍相匹敵的大艦隊,而同時又加速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尷尬情境中(註7)。
這也是當時俾斯麥所極力避免的結果,在俾斯麥的戰略思維中,不列顛即德意志的海權,而德意志亦即不列顛的陸權,兩者應合作無間。任何尋求發展德意志海權的企圖,不僅不應該,而且亦無必要。
英德間的殖民競爭與海軍競賽,不僅導致兩國關係的日形漸遠。更深遠的影響,它開啟英國與法、俄之間彼此進一步合作的空間,英法諒解〈The
Anglo-French Entente〉與英俄諒解〈The Anglo-Russian Entente〉分別在1904年與1907年簽訂,英國終於放棄傳統「權力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加入了集團對抗的陣營中,對於日後國際爭端的互動模式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
「摩洛哥危機」與「巴爾幹戰爭」:逐漸將集團對抗導引至「總解決」的危險思維中
法國不斷尋求吞併摩洛哥的意圖與德國為維護本身經貿利益的干涉行動實為兩次摩洛哥危機的主因。(註8)倘若根據國際正義的立場來觀察事件的始末,很容易發現法國為求吞併摩洛哥,不惜違反與德國之間所達成的協議,甚至以武力介入摩洛哥的政變;而德國在兩次「摩洛哥危機」均處於被動之角色等事實。然而從「阿爾及希拉斯會議」〈The
Algeciras Conference〉與日後英國以支持法國的立場介入德法之間衝突所傳達的訊息來看,協約國顯然在該議題上取得了相當一致的步調.並且主導了國際輿論的方向。而更具指標性意義的發展,便是英法開始尋求雙方國防體系的進一步結合,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緊急狀況。(註9)
如果說兩次的「摩洛哥危機」僅是屬於利益型衝突的「升高」,那麼巴爾幹半島的巨變所衍生的問題則更為嚴重,甚至可能出現立即性的危險。1911年至1913年,巴爾幹諸國與鄂圖曼帝國進行了一次獨立戰爭;之後又爆發了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領導之多國聯軍間的戰爭。
因摩洛哥問題所導致的緊繃局勢,壓縮了主要國家在巴爾幹戰火中的外交運作空間,遂只能任憑巴爾幹半島的權力平衡遭到小國任意地破壞。在這一系列的兢逐中,與俄羅斯關密切的塞爾維亞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兩次的巴爾幹戰爭擴大了其權力基礎。在「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民族激情影響之下,遂開始挑戰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既得利益。(註10)波、赫兩省的地位爭議,以及奧國對塞爾維亞佔領阿爾巴尼亞所採取的干涉行為,均激起了塞爾維亞仇奧的情緒,而這種情緒終於逐漸演變成為實際的政策,也為未來奧、塞雙方更進一步的衝突埋下了種子。
三、「七月危機」始末
根據解密的文件以及學術界的研究顯示,黑手黨(Black
Hand)所一手策劃主導的暗殺行動,塞國政府是事先知情的。(註11)鈕先鍾教授在其相關著作中對於塞爾維亞政府事先知情,但卻沒有向維也納當局提出警告,默許暗殺事件發生的背後考量提出了以下的分析:第一、如果對奧國提出了警告,黑手黨很可能會對塞國的決策高層採取激烈的報復手段。在民族主義高亢的氣氛中,這些塞國領導人對於黑手黨的恐懼程度更勝於戰爭;第二、即使暗殺成功,也不必然就會發生戰爭。況且在必要時候,塞爾維亞可以獲得來自俄國的軍事支持。(註12)此外,塞國政府可能還有一種更深遠的考量,那就是利用因暗殺事件而必然發展的奧、塞衝突,可以將兩國長久以來在巴爾幹半島的矛盾進行一次總解決。
維也納的遲鈍反應與柏林的明確保證決定了事態的進一步的擴大
無論如何,「薩拉耶弗事件」所產生的外交震撼,其漫延速度與影響範圍,已經遠超過塞國政府所想像,國際輿論明顯有利於奧匈帝國對於當前的緊急情況進行明快地處置。然而此時的維也納當局內部,卻在為如何回應的問題上,產生嚴重的分歧與激烈的辯論。以致未能充份利用國際輿論仍對奧國的處境表示同情之時機對塞國採取強硬的政策。
這不僅是因為奧國當局缺乏一種緊急應變的機制以及國內對於和戰問題的分歧,奧國情報單位未能發現塞國政府事先知情之證據,以及奧國陸軍在短期內無法迅速動員集結,都對維也納當局對塞回應的決策過程與方案選擇形成了極大的掣肘。
在奧國漫長的決策過程中,來自威廉二世的無條件保證確實為奧國對塞回應最終轉驅強硬的關鍵因素,儘管柏林方面始終迫切地希望問題的局部化。(註13)德國對於維也納當局所傳達的錯誤訊息,以及後者對於德國支持的認知最終決定了危機的進一步擴大。因為德奧關係在此非常時期的異常密切已引起了聖彼德堡的高度關注與疑慮,亦迫使俄國必須對於該事件進一步地表態,因為俄國與塞爾維亞之間同樣存有軍事支持之承諾。
奧、俄的相繼動員注定將「奧塞衝突」升級成為集團間對抗的最後攤牌
在「薩拉耶弗事件」發生的將近一個月後,奧國終於有了具體的反應,對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於7月23日提出,並限時48小時內全部接受。塞爾維亞顯然擔心讓奧國政府參與暗殺事件的調察工作將可能導致塞國政府事前知情的真相公諸於世,而容許奧國官員參與取締反奧工作亦將使塞國政府多年以來在波、赫兩省所從事的政治滲透與地下佈局功虧一簣。隨著俄國的支持態度日益明朗,貝爾格萊德方面遂無意對通牒內容作完全的讓步與接受,而在此情況下,奧國陸軍開始動員,維也納已決心以武力來解決奧塞之間的所有矛盾,並拒絕任何約束奧國行動自由的國際調停。在確信將能夠獲得來自德國的支持下,奧國甚至相信俄國將不致於甘冒全面戰爭的危險對塞國進行直接的軍事援助。
面臨既將發生的奧塞軍事衝突,協約國選擇以「升高威脅」的手段來緩和當前嚴峻的局勢,並期望藉此來「嚇阻」德、奧在巴爾幹半島的行動。倫敦當局不僅下令英國艦隊進入戰備狀態,同時還鼓勵俄國盡快實施針對奧國的局部性軍事動員。(註14)英國的支持對於陷入長考與立場尷尬的聖比德堡有著極大的鼓舞作用,也使俄國獲至了藉由軍事動員可以迫使奧國停止對塞爾維亞動員的必要信心。
然而,正如奧國陸軍動員的訊息對俄國當局形成莫大的壓力,俄國陸軍在俄奧邊界的動員亦對柏林方面產生了極大的震撼。這不僅僅是因為威廉二世擔心情勢已升高到難已控制的情況,自始至終威廉二世本人均是扮演調解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德國參謀本部擔心俄國的先行動員將抵消德國對法俄的初期軍事優勢,可能將對德軍在執行希里芬計劃時,其東部戰線初期態勢之基本假定與既定佈局構成嚴重的威脅,是此,柏林再一次與聖彼德堡方面的溝通,期望透過說服俄國停止動員作業的進行來尋求局勢的進一步穩定。
單就此一反饋的過程來看,「升高威脅」似乎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至少迫使德國增加對維也納當局的約束動作,並使其再一次尋求以外交途徑解決的可能。然而,如果從更深的層面來觀察,便能發現一項重要且危險的思維正逐漸在各當事國的決策體系中蘊釀,那就是各國的參謀本部對於「動員速度將決定日後初期作戰的勝負」之認知,以及領導階層對於此種憂慮的重視程度,似乎正在逐漸升溫之中,對於各國在危機過程中的進一步反應與行動將出現決定性的影響。
訊息的誤判,俄德相繼總動員,各國依盟約投入戰爭
必須注意一點,俄國所實施的動員作業,乃是針對奧國為的「局部動員」,而非所謂的「總動員」,因此,整個危機似乎仍有和緩的空間。然而倘若俄國以實際的行動介入奧、塞之間的戰爭,那麼德國將會處於一種非常困難的立場。德國將必須遵守「德奧同盟」的規定,依約對奧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然而,一旦德國對巴爾幹半島作直接的軍事投入,英、法將不可能置之不理,如此一來,全面戰爭便無法避免。
德國再一次表達善意,透過外交管道尋求與聖彼德堡方面的再溝通,並且提醒俄方,俄國的持續動員令德國陷入「安全困境」,倘若俄國持續並提升動員的層級與規模,德國將被迫考慮跟進。很可能是措詞使用上的問題,聖彼德堡方面似乎將這項訊息解讀為一種「恐嚇」與「威脅」,俄國認為德、奧間早已存有相當程度的默契,這一次的溝通,很可能是柏林方面故意拖延俄國動員進度,以確保在開戰初期能對俄國保持某種程度之戰略優勢的陰謀。基於此種認知的研判,反而刺激了俄國達成了必須盡快地進一步擴大動員規模的最終決定,總動員令很快地被發佈。
對德國而言,外交途徑的失敗已顯示奧塞戰爭局部化的希望已化為烏有,目前的核心問題已經不再是尋求局勢的緩和,而是盡速完成「希里芬計畫」的準備作業,德國陸軍開始進入總動員階段,並在西部國界逐次集結兵力。
如果此時仍有阻止局勢進一步升高的可能,那必然是指大英帝國的動向。儘管倫敦當局曾經在七月底以下令皇家海軍備戰,並鼓勵俄國動員的方式嚇阻德奧的行動,也曾獲得一時的效果。但緊接而來的戲劇性轉變,卻促使局勢急速升高至戰爭邊緣。
對於是否應以武力支持法、俄抗德,國會與內閣出現激烈的辯論。根據英國的的外交傳統,任何對於歐陸國家的武力承諾都是不能被允許的,除非歐陸的權力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某一個國家企圖獨霸歐陸,或是中立國的地位遭遇威脅時,英國方能取得介入歐陸衝突的使力點。
因此,英國是否投入歐戰或是維持中立的最後關鍵因素,端賴於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是否遭到侵犯。然而各國的參謀本部都很清楚,「希里芬計畫」的設計根本就沒有將比利時的中立問題考慮進來,一旦德軍決定採用該計畫,比利時必然是德軍強大右翼的必經之路。
比利時中立地位的問題終於成為英國投入歐陸作戰的導火線,德國陸軍於8月1日進佔盧森堡大公國,8月3日德、法相互宣戰,8月4日德國陸軍越過比利時國界,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註15)
四、「七月危機」失控原因之檢討
大體上,「七月危機」是以奧、塞衝突為核心,而在歐洲國家彼此交錯之盟約限制下進行外交互動,但衝突卻因當事國普遍性的「安全困境」思維而逐步擴大,最終導致危機的全面失控。
有關「七月危機」最終導至戰爭的責任問題,學術界早有定論。在危機過程中,倘若當事國家採取的行動所依循之中心價值,是傾向於對現狀的改變而非現狀的維持,那麼這個國家對於戰爭的爆發就必須承擔較大的責任。基於這個思考點,法、俄所應負的責任必然要大於德、奧。(註16)
但這並不代表德、奧對於戰爭的爆發可以擺脫一切責任。在瞬息萬變的危機過程中,任何的政策面或是執行面的錯誤,都極可能因為訊息傳達的扭曲而產生致命的結果,基於此點,德、奧的責任並不亞於法、俄。
在危機的過程中,當事國所採取的行動,或是傳達的訊息,往往決定了情勢發展的方向。也因為這些行動及訊息的決策背景與可能產生的「外溢」效應在危機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遂提供了我們極具價值的討論空間與經驗累積。
「戰爭爆發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認知與「盡可能掌握處理時機」的期望,如何影響決策當局的思考與反應?
奧國在「七月危機」中的最大遺憾,就是未能在當國際輿論仍支持其對塞爾維亞採取任何行動時,迅速作出反應。假使能夠如此,這場危機很可能會在對奧國最有利的情況下結束。因為俄國將因輿論的壓力與英國動向不明而難以干涉,而塞爾維亞也將因過去在波、赫兩省惡名昭彰的反奧宣傳與地下策反陷入被動的態勢。從奧國的決策失誤顯示了國家必須預設一種「緊急應變機制」與「標準作業程序」(S.O.P.)的必要性,因為此舉關係到當事國是否能在危機發生的第一時間進入危機處理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反應能力與情況掌握。
在俄、奧在巴爾幹半島傳統地緣衝突的陰影籠罩與攻守同盟的條約限制下,「戰爭爆發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認知直接衝擊領導當局的決策品質。因為「時間壓力」將對理性的思考形成局限,亦可能促使領導當局的思考傾向於「最壞情況」的考慮,這種傾向將會隨著情勢的混沌而逐漸增加其比重,於是「安全困境」的效應將使情勢更為複雜。
具「升高威脅」意義的「準軍事行動」之運用,「期望」與「意外」的平衡點是否可能取得較佳的掌控?
英國艦隊的備戰與俄國陸軍的局部動員,其目的在阻止奧國陸軍進一步對塞爾維亞動員,以求緩和局勢。英國此舉在程度的安排上似乎相當得宜,然而從更深的層面來觀察,便可發現倫敦當局的背後目的與真正期望。英國似乎模糊了危機的焦點與本質,從相對正義的觀點來看,奧國絕對有權對塞爾維亞進行動員,甚至採取某種程度的有限懲罰。然而,在倫敦當局對德、奧展示武力,要求其行動有所節制之時,卻沒有同時對塞爾維亞提出相對應的緊急呼籲,例如要求其對最後通牒重新考慮等。倘若能如此,在德國的壓力下,奧國將很可能對於是否交由國際斡旋重新思考,而後續的處理應會較為容易,至少能夠將局勢真正的緩和下來。
顯然在英國當局的處理思維中,結盟對抗的情結已高於對於危機,甚至衝突進行根本解決的期望。英國的真正態度對於危機的持續延伸當然有其相當程度的響。
「軍事戰略」在國家戰略的位階與緊急應變機制建立之重要性
當德、俄雙方在聖彼德堡進行關鍵性的談判時,純粹軍事性的觀點在決策系統中已佔有相當程度的地位。「安全困境」與「軍事動員計畫」對於雙方談判的底線與解套可能性的探詢形成了極大的糾葛與掣肘。雙方的參謀本部都是依據事先完成的戰爭計畫與開戰的程序規則來影響,甚至限制決策者的選擇。俄國為了取得初期的兵力優勢,片面擴大了動員的規模與層次,以至危機中後期欲求局勢和緩的希望幾乎不可能;德國為求執行「希里芬計畫」,不惜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地位,而終使英國獲得介入歐戰之口實,軍事計畫與政治脫節至此,實乃危機最終失控的關鍵因素
「軍事同盟」對危機處理過程產生的掣肘
無論「德奧同盟」、「法俄協約」等同盟條約均有類似之軍事攻守互助秘密條款。法、俄間的軍事協定之目的,就法國而言,實為對德復仇與收復亞、洛兩省之先期部局;而俄國而言,則為能在近東與巴爾幹遂行權力擴張時能與德、奧形成戰略抗衡之局面。英、法間之軍事協定亦針對德國為假想目標,而此種取向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後更形明顯。相對於德、奧同盟的目的僅為自「普、奧戰爭」結束,雙方關係正常化後,所持續維持的傳統邦誼與基本利益,其目標確不能等同視之。在危機過程中,協約方面交錯的同盟體系不僅對「中歐同盟」的外交努力形成掣肘,對於英、俄、法在危機處理之手段上,亦出現極大的限制,實屬可悲。
五、結論與啟示
「俾斯麥體系」的成功與證明了「預防性外交」的必要性,此為降低全面性國際衝突機率之重要機制;而「國際仲裁者」的維成亦為確保體系穩定之重要關鍵,保證「歐洲協調」均勢結構能持續維持之「不列顛和平」即為重要典範。
然自冷戰之後,國際政治體系重返「兩極對抗」之緊張情勢,大小危機層出不窮。核武的出現與威脅相對化似乎有助於強權領導人重新思考危機解決之可能途徑,避免全面戰爭逐漸成型為決策思維的最高指導,從「古巴飛彈危機」似能窺其一二。
冷戰結束以後,全球性的核戰威脅已不再出現,然原先受壓抑之區域問題與種族矛盾卻因此得以解除束縛。巴爾幹半島的種族混戰,印、巴的核武競賽與喀什米爾武裝衝突,以、巴之間的武裝衝突,以至足以憾動東北亞區域穩定的台海衝突均有升高與擴大之潛在陰影。情勢的控制端賴於暢通的溝通管道與建全的協商機制,而上述均為廣義的危機處理所必須之預防性策略。
歷史的經驗能夠告訴我們那些路是不能走的,卻不一定能夠指引未來。隨著國際溝通網絡的成熟發展,「綜合性安全」概念的逐步建立,國際典範(international
regime)的區隔呈現了世界的複雜性與多樣化。區域內與區域間的經貿競合增加了國際間的互賴程度,對於戰爭爆發的機率似乎有著某種程度的抑制力。然而國際互賴的增加與戰爭的或然率是否真存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日益複雜的國際關係,對於危機的預防與處理究竟會出現怎樣的制約或是契機?而這些都是我們正在面臨的挑戰。
註釋
註1:鈕先鍾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台北:燕京,1977年),
頁209。
註2:周煦著,『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台北:生智,1999),
頁21。
註3:林文程著,【預防外交與台海兩岸關係】,『戰略與國際研究』第三卷第一期(台北:台灣綜合研究院,2001)頁39。
註4:同註1,頁22。
註5:同註1,頁18。
註6:王高成著,【「安全兩難」下的兩岸外教競爭】,『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六卷第十二期(台北:政大國關中心,1997)頁23。
註7:同註1,頁200。
註8:同註1,頁35-37。
註9:同註1,頁56。
註10:同註1,頁69。
註11:同註1,頁84-85。
註12:同註1,頁92。
註13:同註1,頁89。
註14:同註1,頁98。
註15:同註1,頁130。
註16:同註1,頁140。